别在关键的时刻示弱
近期,一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要如何带来改变?如果改变是可能的,那我们要做些什么?
改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仅靠想法和直接的主张难以促成更深远的变化。在看理想主讲人杨照看来,当下需要重新体会哲学家韦伯的思想,在社会思考上,悲伤是一种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退缩不前,而恰恰代表着郑重行动的开始。
关于如何坚定信念、做出行动,杨照结合个人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弱势者无论如何都要相信,你所经历的不平等、不正义、不公平,应该要改变,也能够改变。
讲述 | 杨照
来源 | 《认识现代社会的真相:韦伯60讲》
01.
改变社会前,
要先思考这个社会
我的人生,在20多岁一直到40岁左右的时候,受到过来自社会非常强烈的冲击。后来阅读韦伯,以及呈现韦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迫切的需求,即我必须知道:个人到底应该要如何思考社会。
稍微回到少年时期,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就是大家会直觉地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当做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即使当时没有用“社会”这样的名词,也会很容易觉得我不喜欢我活着的环境,我对于这样的社会,有很多的抱怨、批评。
但是再稍微成长一点,从少年到成年,就会出现一个变化:如果对当下不满,必然面临着选择,是等待他人来替我们打造一个新社会,还是自己去着手改变。
在着手参与改变社会之前,首先要思考这个社会。什么叫做社会?从事实上讲,社会由许多人所组成,单凭自己一个人,要如何改变庞大的社会?并且,你凭什么去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

年轻的时候,我产生了巨大的困扰,一方面觉得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是应该做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惶惶不安,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要怎样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不会感到愧疚?
那个时候虽然我念的是台大历史系,但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台大,常常去辅仁大学的一个社会科学图书馆里看书。馆里有非常完整的现当代社会学的藏书,我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他们是当时的两位社会学大师,主要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逐渐了解到社会学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刻画出社会结构图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没有办法评断,甚至连描述都很困难。至于要如何评断、描述,会涉及到另一个部分,即集体的行为,如果找到了它在结构中的位置,它会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结构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功能。
所以社会学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结构给画出来,再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功能。
02.
在社会思考上,
悲观是一种责任
但用这种方式看社会学,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它都会在社会里扮演一种功能,这不就是黑格尔经常被误解的那句话“凡存在者皆合理”吗?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不应该被拿掉。这样所产生的社会图像,几乎必然是静态的,而且必然是保守的。
虽然塔尔科特·帕森斯特别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说还有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但是读来读去,这不是我当时心目中为了改造社会,要去了解社会的方式。
于是我接着读了《From Max Weber》,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本韦伯选集。尤其是读到演讲词《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以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开展了我全新的视野,其中对我产生最大冲击的是“悲观之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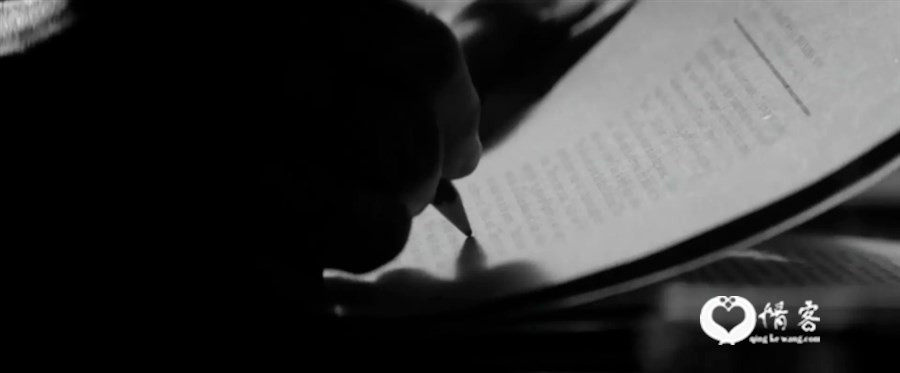
首先,以前看待这个社会,义愤填膺地想要改变它的时候,我很难想到在行动之前还要分辨乐观的方式和悲观的方式。
韦伯很悲观,他的悲观贯彻在他的整个人生乃至于他所有的社会学概念和社会学的研究上。我们不可能忽略韦伯的悲观来认识韦伯,进入到他的社会学世界里。
我们一般想要改变现状的时候,会想要往前冲,把这个打掉,把那个改掉,拿到权力,继而实现想要的改变,但韦伯却告诉我们, 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因为悲观,所以看到未来的时候,不会只凭冲动行事。
韦伯会问,如果失败了,用这种方式做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结果,该怎么办?如果你想要改变的那些反制的不只是你,而反制于现实的状态,该怎么办?如果得到了想象中的权力,但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该怎么办?这一连串的怎么办,就来自于他的悲观。
这样的一种悲观和历史就有了重合之处。因为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改变者必然是乐观的、昂扬的,相信自己当前所使用的手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对的世界。
但或许行动到后来转头酿造为灾难,就来自于过度乐观。在这里,韦伯的悲观就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对质。
03.
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
如果大家曾经听过《八分》(第346期)中我和梁文道的对话,我想特别补充说明,我完全了解文道的悲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悲观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不知道,我是没有资格跟大家讲韦伯的。
我和文道在这一点上的确有所分歧,因为我还有另外一种态度,我不得不坚持,因为我知道这句话: 弱势者没有悲观的权利。

长久以来,在看待社会问题时,我始终习惯站在弱势者的角度来看。弱势者为什么没有悲观的权利?因为如果一个弱势者,一个被欺负的人,一个已经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的人,还要悲观,那就很容易使得你的悲观态度变成逃避的理由。
你就说,这是没办法改变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没有任何办法。这不就是因为悲观,所以被动地接受所有不合理的待遇吗?
弱势者无论如何都要相信,你所经历的不平等、不正义、不公平,“上欺下、多凌寡”的情况应该要改变,也能够改变。这样你才会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维持希望。
在这样的情形下,要试着学会平衡。简单来说,就是尽可能让自己随时都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或者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这才是我始终不变的立场跟态度,也是我在解读韦伯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体会我最在意、最坚持的重点。
04.
我的“狐假虎威”
有人说我的自我很强大,所以才会选择走这样一条路。我的自我真的强大吗?容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应。
李敖80岁的时候,写他的自述,里面有一段非常奇怪的文字,他讲了驯兽师的故事。
面对猛兽,驯兽师有他们的技巧和独到的能力,才能够驯服猛兽。所以驯兽师经常是世袭的,爸爸教给儿子,儿子再教给孙子。但无论再怎么老练,驯兽师还是有被猛兽吃掉的风险。
李敖非常少见地说道,他小时候,最想做的就是驯兽师。
我们从来不知道李敖的梦想是当驯兽师,可是如果他梦想当驯兽师,为什么他讲的故事,是一个老驯兽师终究被狮子吃了?
李敖就说,驯兽师最大的秘诀,就是他明明恐惧,明明力量远远不如这些猛兽,可是他就是不能让这些猛兽知道,他要让猛兽以为这个人比我厉害。因为他比我厉害,我不敢去试,猛兽才会乖乖地听话。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强弱关系,所以一旦一只老虎愿意试一下,驯兽师就会被吃掉。
这样的关系很微妙。李敖的生命力很强大,他曾在一个非常时期,成为一个人物。现在回头想,他在80岁的时候,讲了最真切的话,因为他一直在当驯兽师。
从前,他把自己形象建立起来,让他的敌人搞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底细。在这种状况下,敌人就没有办法伤害他。更进一步的,他就有能力,至少有可能,改变被他的敌人所控制的世界。

我想借由这个故事,很诚实地回应,我没有什么强大的自我。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我不得不走,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因为我对现实有不满,我有理想。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坦白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必须找不同的方式“狐假虎威”。
你明明没有那么大的生命能量,没有那么强大,可是你不能在某些关键的时候示弱。作为一个弱势者,要怎么办?有时候,就是必须要狐假虎威。
我的虎威分成两方面。一种虎威,就是去了解像马克思或者是韦伯这种有洞见,而且懂得表述他们对社会的分析跟想法的人。当我想更进一步地认识这个社会时,我就把马克思搬出来,就把韦伯搬出来。
把他们搬出来,不是把他们当标准答案,而是借由他们,让我可以有信心地说,在当前的状况下,我们的阶级关系是什么?在当前的状况下,我们的官僚体制中的工具理性发展到什么程度?
这不是我说的,不是我有限的生命力量、有限的智慧能够想得出来的——是马克思给我的,是韦伯给我的。
我站在马克思跟韦伯的肩上,你就不能小看我,我可看见更深刻,更准确的社会。我尽可能透彻地了解马克思和韦伯,就是我的“狐假虎威”。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弄清楚,别人拿来控制你、威胁你的东西,实质究竟是什么?例如,如果有人拿赚钱来压制你,你一样可以回归马克思和韦伯。借由他们的视角,你可以把人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想清楚。
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原本使你害怕的东西,可能并没有那么可怕,它或许就是一只纸老虎。
还有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面对某些权力时,我们以为这些权力会用来对付我们,如果你想得更清楚,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权力应该和我们站在一起。只要你不被蒙蔽,把一切看清楚,分析清楚,就能得到勇气,去追索,去建立从自我到社会的一种理想。
热门文章
- 1大学教师体验外卖生活走红,一个月挣了7000多,瘦了6公斤!他说:没有切肤之痛,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
- 2前十一月A股又是全球垫底
- 3抓牢五年一遇的战略性投资机会!最低三折起、最高优惠三万元,总有一款适合您!
- 4让极暗成为过去,让光明普照未来 ——情客旅行 陈炜 年终致语2021
- 5党中央:各级党委和政府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统筹安排好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一体化系统
- 6作家陈炜写给父亲催人泪下的祭文
- 7凤鸣龙跃联盟成立,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优质高效服务于民
- 8卖掉老婆去炒股的股票投资“神投手”,重现“江湖”,股民救星来了
- 9作家陈炜写给父亲催人泪下的祭文
- 10股票投资“神投手”,准确预测股市涨跌,为投资者带去丰厚回报



